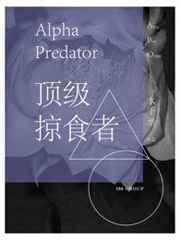莊子(上):永恆的鄉愁
《風流去》轉載請註明來源:繁體小說網ftxs.net
一
在先秦人士中,莊子是很獨特的一位,我認為當時沸沸揚揚色彩斑斕的文士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像蘇秦、張儀,唯利是求,沒什麼特操與價值標準,只要有官做,能富貴,既可懸頭於梁刺股以錐,也可以朝秦暮楚,賣友求榮。而他們中的走運者,最終也進入了實際的政治生活,成為統治者中的一員。合縱連橫,權傾朝野,名滿天下。《孟子》中載景春對孟子的話說:「公孫衍、張儀難道不確實是大丈夫嗎?他們一怒諸侯便恐懼,他們安居不動,天下也就安定無事,」可見他們的顯赫與威風。縱約長蘇秦「位尊而多金」,風度翩翩地來往於六國之間,身兼六國相任,皮包中裝着六國的相印,碰碰撞撞的作着舒心的響聲,連他的父母都灑掃而郊迎三十里了。一部《戰國策》說盡這些人槓桿天下之勢。這頗使第二類人如孟子者滿腹酸醋。孔墨孟荀等人,有自己的哲學,有自己的價值觀,並堅持不放如同身家性命,且還負有一種「有道則出,無道則隱」的氣節,故而也就只能常常不得志,常常對諸侯發牢騷,對第一類人吹冷風了。他們暗中羨慕第一類人,卻又只能冷眼旁觀,眼看着人家把天下鬧得動蕩不安,沸反盈天又一塌糊塗,而自己的呼聲愈來愈被淹沒了,愈來愈受諸侯的白眼了,便只好退回房裡,把滿腔不平和才氣都寫在竹簡上,給後世留下一部部好文章。但以上兩類人雖有大區別,亦有大相同,他們都熱衷於都市生活,喜歡在人群中出風頭,搶鏡頭。孔子在野外的時間不少,並且也頗受苦難磨鍊,但他那輛常由他自己執鞭駕駛的在阡陌間奔馳揚塵的車馬,其轍印是直通城市,且直通諸侯的官邸的;孟子一生足跡不出齊稷下,魏大梁和滕文公的衙門;韓非出身韓國貴公子,更是自小在鬧市中廝混;墨子呢?他出身「賤人」,但他也是城市中的手工業者,並且他的主要活動是以城市及諸侯這個背景展開的。另外,這些人還汲汲於從「治於人」變為「治人」,並津津於研究如何「治人」。由此,以上兩類人都是城市文化的代表,是熱鬧場中的人物。
而第三類,除了一些在歷史典籍中忽隱忽現撲朔迷離的隱者外,有大著作大人格且以大背影遮擋後世的,就只有我現在要寫的這位表情古怪的冷嘲大家莊周先生了。當別人在都市中熱鬧得沸反盈天爭執得不可開交時,他獨自遠遠地站在野外冷笑,而當有人注意他時,他又背過身去,直走到江湖的迷濛中去了,讓我們只有對着他消逝的方向發獃。他是鄉野文化的代表,他的作品充滿野味,且有一種濕漉漉的水的韻味,如遍地野花,在晨風中搖曳多姿,儀態萬方,神韻天成。如果說孔孟荀韓的著作中多的是社會意象或概念,充斥着令人生厭的禮呀、仁呀、忠恕呀、戰爭呀、君臣呀的話,那麼他的著作中卻是令人心脾開張的新世界,一派自然的天籟。這裏生活着的是令人無限景仰的大鵬,怒氣沖沖的擋車的螳螂,自得其樂的斥,以及在河中喝得肚皮溜圓的鼴鼠,這些自然意象構成了他的著作中獨特的魅力。他一生沒有在大都市裡混跡過,官也只做到漆園小吏,大概比現在的鄉長還小—並且決沒有貪污索賄。所以他不但沒有大宗遺產留給兒孫,便是他自己,也窮得向監河侯借糧。監河侯知道這位庄先生借得起還不起,就巧妙地拒絕了。後來他便只好以打草鞋為生。據他的一位窮同鄉—不過後來發了跡—「一悟萬乘之主而益車百乘」的曹商的話,當曹商從秦王那裡得到一百輛車的賞賜,高塵飛揚地回鄉炫耀於莊子時,他見到莊子已窮得「槁項黃馘」—脖子乾枯而皴,麵皮削瘦而黃了。不過此時莊子的智慧與幽默還依舊煥發且銳利無比,使得這位曹商先生反顯齷齪了。他含蓄而尖刻地譏刺曹商舔了秦王股溝中長膿的痔瘡,這種譏刺後來成了中國民間譏嘲拍馬者的成語。
莊子的鄉野文化特徵及其挨餓本色,都是先秦其他學子所沒有的。比如孔子,假如他真的「自行束以上吾未嘗無誨也」,他也有三千塊臘肉了。所以他能「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肉要切大小相同的正方形,再加上生薑細細炖爛,這才下箸。而且酒量特大,一般是喝不到失態的地步的。孟子呢?帶着他的眾多門徒在齊宣王那裡一面大吃大喝,一面又發「君子遠庖廚」以及「萬物皆備於我」的既清高又瀟灑的言論,齊宣王甚至要給他在國都正中蓋別墅,再用萬鍾谷祿來養他的弟子哩。由此可見,莊子的獨特,挨餓本色村夫家相是其一。
不過這裏得交待一句,莊子並不是沒有城市戶口,不願在城市裡做盲流才住鄉下的—他本來至少可以到城市開一個鞋店,乾乾個體經濟,說不定還能暴發—莊子之住鄉下,乃是他死心塌地的選擇。楚王曾派人去請他,說願意以天下相煩,客氣得很,但此時莊子正專心致志地在濮水上釣魚,眼神直盯着水面上的閑逸的浮子,沒有理會這飛黃騰達的機遇,冷冷地把使者打發走了。而他自己像個真正自由的野田之龜,弋尾於塗,雖則不如孔孟炫赫與實惠,卻其樂無窮。他的這種心境實在是人類心靈的花朵,永遠在鄉村野外幽芳獨放,一塵不染,誘引着厭倦城市生活的人們。
莊子的第二個獨特之處在於,他是先秦諸子中唯一不對帝王說話而對我們這些平常人說話的人。當別人都在對着諸侯不甚耐煩的耳朵喋喋不休地說著如何如何「治人」的時候,莊子轉過身來,懇切而激動地告訴我們如何自救與解脫,如何在一片混亂中保持心靈的安寧與清凈,如何在醜惡世界中保持住內心的自尊自愛,不為時勢左右而無所適從,喪失本性,以及如何在「無逃乎天地之間」的險惡中「遊刃有餘」地養生,以盡天年。無疑,他是較為親切的。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說莊子哲學「專在破執」,可謂一語道破,很多我們執著不放孜孜以求的所謂價值,到底對我們心靈有什麼好處呢?「破執」後來是佛教的特色,難怪《莊子》一書被後世的道教徒稱為《南華真經》而與佛教抗衡呢。
二
莊子也寂寞。他和名聲赫赫的孟軻是同時代人,並且兩人還有共同的朋友(比如梁惠王),但孟子的著作中沒有提到莊子,莊子也沒有提到孟子,可見他與世隔絕得多麼嚴重。我是常常為此感到遺憾的,老子與孔子據說是相見過的,並且有些牾,但這兩人都不善辯論,沒有留下太精彩的對話,一個樸拙深厚,長者風度,言簡意賅;一個彬彬有禮,溫良謙讓,立論中庸。兩個平和的人在一起,是不大能有趣味的。但莊子和孟子就不一樣了,若他倆能相見,一樣的傲慢與偏見,一樣的激情浩蕩,那該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孟子是當時的辯論高手,這方面名滿天下,以「好辯」著稱;莊子呢?言語文章汪洋恣肆,一瀉千里。況且這兩人,一個執邏輯利器,無敵不摧,無堅不克;一個肆詩性智慧,浩浩蕩蕩,大氣包容。一人力距楊墨,一人終身剽剝孔子之道。這兩人若能相見,會在歷史的原野上戰成甚番氣候!會有多少好看的文章傳世!
哲學乃是智慧的對話或碰撞。當代兩位最了不起的哲學家卻如此隔膜,實在叫人費解。梁惠王被李贄貶諷,說其資質太差,我看真有這麼回事,不然,他何不知道引見孟庄兩位呢?
莊子一生中,唯一的朋友是惠施,這兩人中間有不少爭論。總的來說,惠施現實,講實證,恪守物我界限;莊子玄想,講悟性,力主物我貫通。因此,惠施諷刺說莊子的言論大而無當,所以為人所棄;莊子反唇相譏,說惠子被茅塞堵心,不知天外有天,固執無知。這兩人生前有猜疑,並不十分友好,惠子疑心莊子要搶他相位,莊子則刻薄地說惠子是視腐鼠為美餐的鷂鷹。但惠子死後,莊子卻十分悲傷,在惠子墓前唏噓難禁,以「郢人失質」為喻,痛吊這位老對手。因為除惠子外,再無人與他辯論闡發了。這也可見他當時的寂寞心境。
另外,如果不怕別人指我為偏激的話,我還認為,在先秦諸子中,就其著作所討論的範圍和深度而言,真能稱得上為哲學著作的,除了《老子》,也只有《莊子》了。試平心想一想,《孟子》中除了論「人性」的幾節有哲學意味外,其他的不都是談政治甚至政策嗎?
三
更多內容加載中...請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機瀏覽器訪問,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節內容加載失敗,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模式、暢讀模式、小說模式,以及關閉廣告屏蔽功能,或複製網址到其他瀏覽器閱讀!
小說推薦:《天命之上》《玄鑒仙族》《仗劍獨行斬鬼神》《惡龍,為了賺錢選擇文化勝利》【創讀小說】《她被趕出侯府後》《沼澤領主:我有情報系統》《你不許再親我啦[快穿]》《仗劍獨行斬鬼神》《回到過去做財閥》
鮑鵬山提示您:看後求收藏(繁體小說網ftxs.net),接着再看更方便。若瀏覽器顯示沒有新章節了,請嘗試點擊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單,退出閱讀模式即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