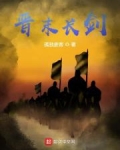揚雄:從向隅而泣到向隅而笑(1 / 3)
一
揚雄在西漢末年,是個不尷不尬的人物,在當時及後世的名聲,也是不腥不臭。我寫他,覺得難,因為他不倫不類;不寫他,也不好,因為他不大不小。弄得我左右不是,就怕寫出來不疼不癢,不三不四,讓讀者讀着不咸不淡,如同嚼蠟。
但揚雄是做「純學問」的人。在學界鼓吹與獎賞做純學問的今天,寫寫他還是有意思的。今天有很多學者在標榜「純學問」,在「學術規範」里操作出不涉當今而傳之後世的偉大學術。並且他們還當自己是前無古人,殊不知在傳統中國,尤其是明清兩代,多的恰恰是做純學問的人,而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則寥若晨星。且據我觀察,在中國,這種「純學問」越發達,越繁榮,所謂「學術成就」越博大,越精深,這樣的學術大師越多,社會生活反倒越萎縮,社會進步越趨於停滯,甚而倒退。這可以稱之為學術中的「零增長」。
揚雄(也可以寫作楊雄,只要不和《水滸》中的潘巧雲丈夫混淆,沒有關係的),乃是純學術之鼻祖。在他之前,無論是先秦,還是漢代人物,如此退守於人間一隅,退守於學問一隅,向隅而泣的人,沒有。
揚雄是不得已的。是別人把他逼到這一學問之隅,讓他在此耗盡青春與熱血的。所以我說他是向隅而泣。別人在那兒玩政治、玩權力進而玩世界,不帶他玩,他只好自己一個人玩兒,玩學術。「純學術」研究從形式到實質都近似於手淫—一種焦慮的自慰。一種無奈的替代。並且通過想像來滿足。當然,政府有時是獎勵手淫的,因為手淫不致於影響別人,符合安定、穩定的大局。清政府就對此特別獎賞。今天手淫的人,也大都做了教授博士了,拿上津貼了。手淫得不夠的人,還在那裡加勁手淫,力爭早日拿到津貼,拿到項目經費。不過,當初揚雄退守學問一隅,乃向隅而泣,漢政府不及清政府高明,不知道通過獎勵把這類人的精血引到學問上去,讓他們為繁榮學術安定團結作貢獻。而清代以降,由於政府的賞賚與誇獎,做「純學問」的學者們乃是向隅而笑—在那裡偷着樂,樂不可支。
二
說揚雄在那時代不尷不尬,我是指他的處境與心境。他歷仕三朝(成帝、哀帝、平帝),又趕上了王莽的新朝。可自從在成帝時因文學創作小有名氣,讓成帝聯想與懷念另一個蜀人司馬相如,愛屋及烏讓他做了黃門侍郎後,到哀、平二帝,竟一直沒能再升遷。三世不升遷,此前大約只有被左思與王勃同情的馮公—馮唐能比。馮唐也是歷仕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而位不過郎署的,左思同情他「白首不見招」(《詠史》),王勃感慨他「馮唐易老」(《滕王閣序》),拿生命去等皇帝老兒的垂青,卻最終人老珠黃,還是不見委任狀。揚雄也一樣長壽,可他的長壽不能讓他在官場上大器晚成,苦盡甘來,倒是應了老子的話:「壽則多辱。」他苟活到王莽新朝,王莽終於提拔了他一下,讓他做到中散大夫。不過,這樣一來,他的名聲—在當時的名聲及在後世的名聲,也就弄得不腥不臭了。班固在《漢書》本傳中這樣敘述:
雄……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
唉,最後「轉為大夫」,還是看他的資歷太老了,人人冠蓋,斯人憔悴,弄得王莽動了惻隱之心。王莽的私人品德本來就是不錯的。至於說他「恬於勢利」,我不大相信,因為有他自己一些發牢騷的文章可證。再者,那個時代,讀書人除了做官,還有什麼方式來體現自己的價值及滿足自己的成就感?以今證古,既然今天的讀書人已經有了更多的體現自身價值的途徑與方式,比如發明創造,比如賺錢,比如做文化名人或罵文化名人,最不濟還可以評教授—教授的待遇據說大約相當於副廳級了—而他們仍最熱衷於做官,那麼,古代的讀書人,憑什麼要淡泊呢?他到哪裡去淡泊呢?我們又有什麼道德優勢要求他們淡泊呢?
事實上,揚雄的「恬於勢利」,不過是在終身不得志既成事實之後的遮醜之辭罷了。這也就是那隻說葡萄酸的猴子的辦法:用貶低自己得不到的東西來擺脫自己的失敗感挫折感。
當然,揚雄的不陞官,自有他的正麵價值,這正麵價值不在於他不想陞官,而在於他雖想陞官,卻不屑於為此不擇手段。要知道,在專制時代,要想陞官保官,往往需要不擇手段,雖然即使不擇手段也未必能陞官保官。所以,像揚雄這樣,能堅持這一道德底線並不容易,尤其是身處一個不擇手段各顯神通以邀官的時代。我們看看他身邊的那些同事都是些什麼人—小白臉兼性倒錯董賢,大奸雄王莽,機會主義者劉歆,還有那一群「用符命稱功德」從而「獲封爵」的談說之士。奸雄王莽與機會主義者劉歆還好,這兩人至少還不讓人噁心。而董賢是什麼人?一個嗲聲嗲氣的白臉小後生,哀帝的同性戀對象。哀帝三千後宮美女都不愛,卻偏偏愛上這個小白臉,每天與他同宿止,那個有名的「斷袖」故事,就發生在他倆身上:一次他倆同宿,董賢睡着了,壓住了哀帝的衣袖,哀帝要起床,卻又心疼董賢,不想弄醒他,便用剪子把自己的衣袖剪斷。
後來,「斷袖」或「斷袖之癖」便成了男性同性戀的特稱。董賢油頭粉面嗲聲嗲氣,我們都可以不管,他有同性戀傾向也可以,但他以此為資本而位至三公,甚至弄得哀帝要把天下讓給他,就顯然壞了官場升遷的秩序,更壞了封建社會的權力交替規則。揚雄是頗以清高自命的,可他偏偏與董賢同官,真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的窩囊。連神經特堅強的王莽,一看董賢受寵,都趕緊打報告回自己的封地去做寓公。揚雄卻只能勉力忍受,這是因為他家裡太窮,他不能沒了那份俸祿。王莽回封地有太后王政君賜的百萬錢財,他揚雄小科長不當只能算是自動離職,或作下崗處理。所以他沒資格沒條件耍脾氣。清高,潔身自好,獨善其身,等等等等,都是要條件的。於是,一肚子窩囊氣的揚雄,大官做不了,小官丟不了,眼前不幹凈,卻還避不了。做官於他,真是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肉。但這無肉,是沒有多少肉的意思,不是全然沒有。這一星半點的肉,於他還很重要,他還要賴以活命。後來,王莽篡漢,他也只能接受任命,畢竟他要吃飯。
可這樣一來,他的名聲,也就被弄得不腥不臭了。這可以說是他自尊心所受的最大傷害。他本來自期很高,年輕時在蜀,還沒有走進社會混事的時候,就寫過一篇《反離騷》,專同屈原唱反調。他認為屈原不會做人,人生智慧不足,所以,死得不值,且死有餘辜。那時他是很自信的,他自信自己可以處理好一切。既可內聖,亦能外王。但他後來做得怎樣呢?
按說,他也不是一個糊塗的人,尤其不是一個無恥的人。當王莽大紅大紫篡代之跡已顯之時,那麼多人用符命稱功德,他頗能自持,沒有同流合污。要知道,他同時代的大學者,漢家宗室劉歆都已倒向王莽成了王莽的軍師了。編造幾句沒頭沒尾的黑話,再釋以沒邊沒際的瞎話,吹捧吹捧王莽,這種造符命的功夫,他揚雄要是願意做,定做得比別人漂亮。但他就是沒有做。按說他夠清白的吧。可不知怎的,弄到最後,還是把他弄了個不腥不臭。原來,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王莽以符命為根據代漢自立為皇帝後,符命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於是他想杜絕符命,以神其事。但有兩個傻子獻符命而上了癮,剎不了車,又給王莽上了新「符命」。這兩個傻子便是甄豐的兒子甄尋,劉歆的兒子劉棻。王莽大怒,殺了甄豐甄尋父子,把劉棻流放邊荒。這事本來與揚雄無關。但揚雄有一個小毛病,他喜歡研究「古文奇字」(這是最純最純的純學問哩),還沒事寫幾個拿出來炫耀。劉棻就跟他學了幾個去。治獄的人在劉棻那兒見了這幾個奇形怪狀誰也不認識的鬼畫符,以為又是什麼符命。一問,乃是揚雄教的,便馬上火急火燎地來抓人。那時揚雄正在天祿閣上校書—好個安於寂寞的書生!天下亂成這樣,他還如此心靜—一看來者凶神惡煞,他又口吃,平時就結結巴巴,期期艾艾,一急更說不清,乾脆從天祿閣上跳下自殺。偏偏天祿閣不高,他只摔個半死,還是被捕進獄中,受那侮辱。後來事情報到王莽那兒,王莽心裏明鏡兒似的,說:「這人從來不參與政事,怎麼也抓來了?」叫人去查。一查,弄清了,那幾個字乃是古文奇字,不是符命,就放了他。可是,京師的童子們早已拍着手唱開了歌謠:
唯寂寞,自投閣。
爰清靜,作符命。
那意思是諷刺他:你不是標榜安於寂寞嗎?怎麼自己從天祿閣上跳下來了?你不是追求清靜嗎?怎麼也作起了符命?這歌謠夠損的。但細細一想,也有道理。躲進學問之中,就真的能寂寞、能清靜么?
中國讀書人,在有關自由空間的態度上,有兩類,一類是不覺得沒有自由空間。因為他們已自覺地成為政統的傳聲筒與維護者,已經沒有獨立意識,自然也就沒有了自由意識,沒有自由意識,自然也就無所謂自由空間:他在鳥籠子里也不覺得難受。另一類呢?是感受到自由空間的狹小逼仄的,但他們不是通過反抗來獲得較大空間,而是通過個體的自我壓縮,尋找與外部環境的妥協,避免與環境發生衝突。或退回內心世界,在所謂的學問之中消磨自己的生命。但這種學問,這種工作,往往既冷僻,又無聊,無趣兼無用,所以往往也無助於社會的進步,無助於自由空間的拓展。所以他們註定只是悲劇角色。
更可悲的是,當他們退居世界偏僻一隅,自以為不找世界麻煩了,但他們不知道世界會來找他們麻煩。我有一熟人,告訴我說:「你們寫文章,犯錯誤的可能性很大。」於是他不寫文章。可後來,我嚴格按照四項基本原則寫文章,至今未犯錯誤,他卻練了法輪功,一不小心入了邪教,信了歪理邪說,真犯了錯誤。我們知道怎樣才能避免犯錯誤么?揚雄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因為很多時候,錯誤不是我們犯的,而是別人鑒定的。
我不知道,揚雄在家卧床養傷時,聽到這樣的歌謠,是什麼樣的心情與反應。他一定心灰意冷吧。但「眾不可戶說」—這可就是他頗不屑的屈原的名言呵,他這時能理解屈原的那種被全世界誤解與拋棄的痛苦了吧—看來他只能隱忍。他身體的摔傷可以治癒,而他心靈的創傷怕永遠難以癒合了。
三
揚雄死後,他的名聲在歷史上仍然不腥不臭。與王莽的關係是他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污點。王莽當了皇帝,他不但沒當前朝遺民,為前朝殉葬或遁跡山林,反而升了一級。這就讓他縱有一千張嘴也說不清。據說他還作《劇秦美新》來稱頌王莽,更為他招來一片責罵。但關於這一點,我願意為他辯護幾句。即便他確實作了《劇秦美新》,秦指暴秦,新,指王莽的新朝。但王莽的新朝是從漢朝蟬蛻而來的,所以,既要贊「美新」朝,應當「劇漢」才對,他為什麼要拿不相關的秦朝來與它相對應?看來,揚雄對「漢」還是留有情面的,是留着感情的,那麼,對這個篡漢而來的新朝的讚美,當然也就留有餘地了。這也算是文人的小聰明吧,這種文人的小聰明其實沒有什麼用處,但在專制政體下,唯這點小聰明可以讓人喘喘氣。也有人說,《劇秦美新》是後人的偽造,非揚雄的作品,這也是出於為他洗刷的良苦用心。
更多內容加載中...請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機瀏覽器訪問,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節內容加載失敗,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模式、暢讀模式、小說模式,以及關閉廣告屏蔽功能,或複製網址到其他瀏覽器閱讀!
本章未完,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若瀏覽器顯示沒有新章節了,請嘗試點擊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單,退出閱讀模式即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