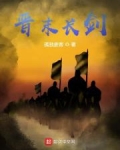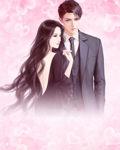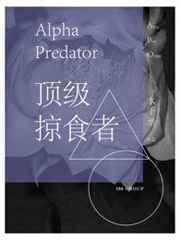仲尼弟子:昨夜星辰(1 / 2)
《風流去》轉載請註明來源:繁體小說網ftxs.net
一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是孔子談政治的話,透露着他的璀璨夢想:他多想能以德行安居政治中心,形成「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大一統」啊。可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如此美好的夢中醒來,他內心一片迷惘。不過,「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孔子為人以德,其人格也如同北斗星辰,而他的那些弟子,則正是拱衞在他周圍的燦爛群星,在那個篳路藍縷的洪荒時代,他們共同構成了吾民族頭頂上深邃而燦爛的天宇。這些昨夜的星辰,至今仍在那遙遠的地方閃爍,向我們送來他們意味深長的注視。
據孔子自己說,他的受業弟子中,身通六藝的有七十七人。這些都是一些極有思想、極有個性、極有血性的人。他們思慮深刻,情感豐富,個個生龍活虎,志向遠大。他們無一絲小兒女態,無一絲求田問舍之想。他們跟隨孔子,顛沛為天下,在苦難中表演他們的風流,在艱苦中顯露他們的卓絕。他們並不完美,但他們追求完美,正如他們生活在充滿缺憾的時代,卻又堅定不移地追求理想的世界。他們並不崇高,但他們決不否定崇高,而是以此懸的,作為自己人生磨礪的旨歸。所以,儘管他們有種種缺點、種種不足,甚至不免偶然也有一些小人作態,但他們仍然可愛、可敬,他們的缺點與不足,正如子貢所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據孔子頗為得意的介紹,在弟子中,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語言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事見長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學(學問)見長的有子游、子夏。這十人後人稱之為「孔門十哲」。其實,孔門高徒遠不止這個數,比如那個成就卓著的曾子曾參就不在此列。《史記·孔子世家》還記載,正由於孔子手下人才濟濟,反而使楚昭王有所顧忌,而不敢分封他土地,怕他有朝一日強大起來,危害自身。
有教無類的孔門私學裏,不僅弟子們出身各異,個性也極豐富。作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並不要求弟子們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對他們各自的個性也能給予足夠的寬容甚至鼓勵,這樣,孔氏私學就獲得了極活躍的細胞,從而保持了強大的生命力與學術創新能力。孔子曾以欣賞的口吻談論他弟子們的個性與天賦:子張狡黠,曾子遲鈍,高柴愚直,而仲由季路則改不掉粗鄙的毛病。顏淵呢?安於貧窮,家裡的米缸老是空空如也。端木賜子貢則不拘泥於老師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的說教,有大興趣且花大精力於生意場上,他的投機活動往往百投百中,從而積聚了大量的財富……但不管他們如何豐富多彩,千人千面,他們仍然是孔子的學生,因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於仁義的信仰,對文化的虔誠,對自身道德的磨礪、人文人格的堅持與發揚,以及,對天下洶洶滔滔罪惡的反抗,對民間苦難的關注,對一切卑鄙政治的高度敏感。他們總是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二
孔子最欣賞顏回,一則曰:「吾不如也」,一則曰:「吾為爾宰」,慨嘆自己不如這個顏家小子,並祝福貧寒病弱的顏回能多多發財,然後自己去做他的管家。我也先寫寫他。不過,我對顏回的看法,與孔子做的鑒定有些出入。老實說,我對顏回的印象不大好。這可能是由於我對一切道德楷模的過敏性反感,顏回就是孔子推薦出來的道德楷模。在一個張鐵生都曾成為我的榜樣的人生經驗中,我不能不小心地對待一切推薦的人格模範。我真心又放心地向我的鄰居學習勤勉,向我的同事學習忠厚,向我的一位領導學習關心人,以及,更早的,向我的父親學習正直與對萬物的仁慈,向我的母親學習無私的奉獻……這些人都是我自己能觸摸到的,而且,他們也沒讓我向他們學習。人們往往有一種逆反心理,即便是他們本來想要的好東西,一旦有人向他們喋喋不休地推薦,他們馬上就會棄之不顧:他們懷疑推薦人的動機。孔子推薦顏回的動機是什麼呢?這是一個我不得不小心的問題。顏回沒有一點實際事功,也不見他對實際事務流露過什麼興趣,在孔門弟子中,顏回一直是一個袖手旁觀卻又時時發些高妙之論的人物。孔子曾誇獎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我倒覺得他的這種無可無不可的神情太過冷漠,很不像孔門弟子的整體作風,不像春秋戰國這個「軸心時代」的精神風貌,倒好像和二十世紀末的一些解構主義者們有些相似。我該不會把對各種「後」主義的反感移到「先」秦的顏回身上了吧?
顏回深受孔子賞識,我以為有兩個原因。一是顏回乖順;二是他早死。早死,好多毛病還沒暴露,留在記憶中的就是一個純潔小青年的模樣,在時時的回憶與追悼中,這個楚楚可憐的模樣兒會平添多少傷感?顏回,這枝病弱的花朵,孔子曾經是希望他能結出一個大大的果子來的啊。這枚果子雖沒有物理性地成為現實,但在孔子的心理上,它是那麼一種真實的、刻骨銘心的存在。誰能在凋落的花蕾中看到期待中的果實化為一夢,誰就是不可救藥的感傷主義者。在孔子「天喪予!天喪予」的慟哭中,我們是否心碎於老聖人的又一次失敗與絕望?
所以,我以為,孔子在顏回死後不斷地推重他,乃是一種心理的需求。他已看見自己黯淡的未來,他已無力把握未來,他已無力推開失敗,他太疲倦了,他也早沒有自信了,他渴望有人早一點接過他的「斯文」之棒,替他跑下去,可是,正當他想着把接力棒傳給對方時,對方卻先倒了下去,這是多大的打擊?在強烈的挫折感與世界的冷酷中,死者顏回那記憶中的容顏是他無法忘卻的遺憾,是他又一次失敗的象徵,也是他心頭唯一的溫暖……
顏回是那麼乖巧,乖巧的孩子或孩子的乖巧是老人晚景中最順心的拐杖。顏回是一個善解人意的人,他知道老師在現實政治中碰過太多的釘子,受到不能挽回的失敗,所以,他盡量避免和老師發生衝突,以免傷害老師那顆疤痕累累的心靈。他從不在老師說話時有什麼反詰,「不違如愚」。在這種場合他往往呆若木雞,又唯唯諾諾。即使不明白或不理解,他也等着退下來後自己去琢磨。這也是孔子讚賞過的那種常人「不可及」的愚吧。問題是,顏回的這種做法,難道不是恰恰違背了老師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教導么?況且,既然當場已經表示附和了,退下來以後的琢磨領悟,怕也只能堅持「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原則了。這實在夠不上孔子所說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至少他不直。對此,孔子也似有微辭:「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顏回不是那種能助益我的人啊,他對我說的話沒有不喜歡的。我們現在有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孔子絕對正確,永遠正確,事無大小言無巨細一概正確,所以,對顏回的這種「無所不悅」,也就視為他一心向仁的美德了。但假若我們認為孔子之言亦有可商榷處,像顏回這樣,就只能是非佞即詐了。實際上,孔門不少弟子都是敢於和孔子「商榷」的,也正因為這樣,才使得「教學相長」,不僅有助於學生,還有助於孔子本人,顏回這樣的「先生步亦步,先生趨亦趨」,只能是使老師和學生一起沒出息。
顏回還有一些便辟善柔的「損者三友」的毛病。孔子被匡人圍困,好不容易才得以脫身,顏回最後趕到。孔子心有餘悸地說:「我以為你已經死了。」顏回竟說:「先生還在,我顏回怎敢死?」我想,死與不死,當時是取決於匡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選擇權豈能在魚肉?顏回為了討老師的歡心,不僅藐視匡人的刀俎,而且還藐視大自然了。藐視大自然,怕也會「不得其死」吧。「回年二十九,發盡白,早死」(死時年三十二),偏偏死在孔子的前面了,弄得孔子呼天搶地地痛不欲生,這回他怎麼敢死了?若真像他所說的那樣,要苟活一條命以侍奉老師,他為什麼不想些法子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營養狀況,而是甘心每日一簞食一瓢飲地糟蹋自己的生命?孔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照顏回的說法,倒好像死生由自己決定了。欺人,欺天,還欺師,文弱虔誠的顏回,總給我一種不真實不踏實的感覺。
孔子說:「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這話不假,有顏回的便佞善柔做榜樣,有老師的頻頻讚譽做導向,門人豈不都學顏回,一個個以乖巧順從來討老師的歡心?
顏回贊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未由也已。」這個在孔子面前完全喪失自我的顏回,顯然已經手足無措,精神恍惚了。孔子忽然在前,忽然在後,這簡直是白日見鬼了。顏回至此,已無生路可走,只有一條死路。這回應該是「先生在,回何敢活」了。
不是物質上窮死了顏回,而是精神上的窮途末路。我斗膽說,顏回死於神經衰弱。
三
曾皙曾參父子都追隨孔子。孔子曾說,曾皙和漆雕開「已見大意」,可見修養的大體已具。孔子和子路、冉有、公西華及曾皙談志向,輪到曾皙時,曾皙竟說出一段詩情畫意的話來—「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一下子把孔子感動得心曠神怡,喟然嘆服。有人把這幾句意譯如下:
二月過,三月三,
穿上新縫的大布衫。
大的大,小的小,
一同到南河洗個澡。
洗罷澡,乘晚涼,
回來唱個「山坡羊」。
更多內容加載中...請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機瀏覽器訪問,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節內容加載失敗,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模式、暢讀模式、小說模式,以及關閉廣告屏蔽功能,或複製網址到其他瀏覽器閱讀!
本章未完,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若瀏覽器顯示沒有新章節了,請嘗試點擊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單,退出閱讀模式即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