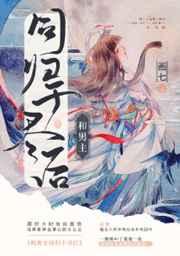卡米爾·克洛岱爾
竭寶峰提示您:看後求收藏(繁體小說網ftxs.net),接着再看更方便。
卡米爾·克洛岱爾
卡米爾·克洛岱爾,19世紀末法國雕塑大師羅丹的情人、學生、模特兒,一位才華橫溢的雕塑家。1883年,漂亮而極富雕塑才氣的卡米爾闖進了羅丹的生活,此時羅丹已是舉世聞名的大師,但43歲的羅丹與19歲的卡米爾一見如故,兩人從此一起分享藝術和生活的樂趣。在同居的15年中,羅丹在藝術上達到了高峰,創作出《達娜厄》、《吻》、《永恆的偶像》等象徵著兩人情愛的作品,而他的代表作《地獄之門》也有相當一部分的作品構思和構圖來自卡米爾的雕塑。這是羅丹一生的黃金時代,他享受着藝術家和情人的雙重快樂。雕塑史上關於卡米爾的敘述止於這些,卡米爾是首先作為羅丹的情人存在,然後才是雕塑家。
1988年,法國演藝界的奇女子伊莎貝爾·阿佳妮傾注全部心血,將卡米爾的故事搬上銀幕,終於揭曉了這段雕塑史上刻意保持的空白。這部長達兩小時的影片以少有的細緻描繪了令人心碎的、一個生命毀滅的全部過程。大師的醜陋是無可逃脫的話題。只因為貪圖現成、安定的家庭生活,羅丹背棄了他的情人,但可笑的是那位迫他就範的「妻子」,也只是一個沒有名分的情婦。關於這位和羅丹一起生活到終老的「妻子」,我們知之不多,只知道她容貌平庸,趣味低下,待人刻薄,為羅丹生育過幾個孩子,而且比羅丹大好幾歲。這位「妻子」一發現羅丹和卡米爾的事,就威脅卡米爾離開羅丹,甚至拿着兇器試圖傷害卡米爾。在這個女人的咆哮面前,羅丹顯得懦弱而無能,根本無法保護脆弱的卡米爾。當有人開始攻擊卡米爾抄襲羅丹的作品時,羅丹也沒有能力澄清卡米爾的屈辱,最終導致兩人的決裂。即使是大師,也並非足以支撐一個女子的情感與理智。一座宮殿,你搗毀了它,就再難修補。她說:「我無法和別人分享你,那對我是一種掙扎。你錯以為那是與你有關的,其實我就是那個老婦人,不過不是她的身體;那年齡增長中的年輕少女也是我;而那男人也是我,不是你。我將我所有粗暴的個性賦予了他,他用我的虛空給我作為交換。就這樣,一共有三個我,虛空的三位一體。」
當卡米爾的目光由純真變為惡毒,當她由才華橫溢流落到醉眼醺醺、一無所成,當那張天使般的面孔變為千瘡百孔,請注意那些面孔:像星光一樣微弱,像美麗的星光淹沒在冰冷的宇宙當中,茫然不知所措。這是一個被事實的陰影毀壞了的生命,毀壞了的女人。陰暗的地下室里,我們看到卡米爾赤裸着身子,弓着背,手中的泥巴瘋狂地左右塗抹,嘴裏艱難地呻吟着。這已經不是藝術,不是創作,而彷彿是一個人臨風站在生命的邊緣不寒而慄,任憑瘋狂像罡風一樣強大,粗暴又野蠻地拉她人胸懷,一起發出野性的呼喚。她的屋子比地窖還要陰冷,塞納河陡漲的河水使它更像被淹的古墓。
這個桀驁不馴、永遠學不會循規蹈矩的女人,這個永遠喜歡漫無邊際地狂奔,而不是安安穩穩地沿着既定路線行走的女人,這個永遠只聽從自己內心的呼喚,只回應遙遠曠野的原始呼喚的女人!卡米爾的一生都在狂奔,也許因為她知道自己可以經過的時間只有別人的一半--她的另一半人生將寸步難行,被那件束縛瘋子的緊身衣牢牢捆住。
可以說羅丹從未正視過卡米爾的才氣,他不願正視,或是說不敢正視,因為她實在是太光芒四射。他把她當成一個他極力想佔有、征服的女人。卡米爾最終得以進入羅丹的世界,是通過以自己為模特完成的。女性,在這裏又化為被「看」,被「塑造」的對象。因而可以說,她以這種方式介入的本身就預示着其不可靠性,她的才華被降到次要的因素,重要的是她激起了羅丹的靈感和慾望。女性的才華始終沒有得到承認,她是作為慾望的客體,以自己的身體當成入場券而登堂入室的。卡米爾追隨羅丹來到巴黎,但她並不是作為獨立的創作個體,而是羅丹的雕塑對象、靈感源泉。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指稱着「匱乏」的女性在此卻擁有男人失去的東西,她們被男性暗中嫉妒着。儘管如此,她們也不能得到與男性平等的權利。事實是,她們反而被一點點地磨去自己的稜角,被迫拋棄過去。卡米爾與家人疏遠了,即使是一直以來默默支持她、相信她的父親以及和她無話不談的弟弟;她也失去了昔日的創作夥伴,卡米爾的創作個性--她找不到了,在羅丹的陰影下。而羅丹則「偷窺」了她的靈氣,利用了她,確切地說是剽竊了她的才華。權威的力量不容被逾越,而只能利用來埋葬女性。他企圖把她固置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從而永遠地佔有她,遮蔽她。但卡米爾較之一般的小有才氣的女人不同之處在於,她是一個蘊藏着不可遏制的能量與激情的女人,她無法忍受自己被男人操縱,她身上那股本能的衝動太過強烈。雖然在這中間,她曾經有過為在愛情上得到承認而妥協的幻想,但羅丹的自私打破了她的夢。從根本上說,羅丹愛卡米爾是因為她具有普通女人沒有的靈性,她是個「特殊」的女人;但同時他又不承認她的能力,因為她是女人。這種雙重的否定使得卡米爾無論是作為傳統意義上的女人,還是藝術家都失敗了。在這兩個層次上,她都被拋棄、摧毀了。
當卡米爾發現自己其實只是「羅丹的工人、模特、靈感的啟示者和女伴」,她為自己工作得不夠,她棲居在羅丹的陰影中,永遠不可能獨立的時候,卡米爾在絕望中全身心地投入雕塑中。在那件以她自己的身體為模特的傑作中,「她的迅速有力使他感到震驚,大膽的姿勢使他心緒紛亂」,卡米爾那種使人產生肉慾的雕塑才華讓世人受不了,也讓羅丹感到害怕,因為在凝固的石像下面,沒有人可以假裝看不見那狂奔歡呼的慾望。但卡米爾的成功只是招來了「仇恨、嫉妒、誹謗、沉默或者冷淡」,人們懷疑她只是在模仿羅丹,甚至懷疑是羅丹替她做的。卡米爾的大膽僭越和挑釁,終於讓她一步一步付出了代價:羅丹的背叛,世人的白眼,藝術之路越走越狹窄,精神壓力越來越大,瀕臨崩潰邊緣--最致命的一擊是,流產使她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孩子。羅丹對卡米爾作品的公然剽竊,徹底打消了她最後一絲眷戀,她感到了從心底升起的陣陣寒意--她和她的雕像一樣,被放在展覽的出口處,在太陽下暴晒,落滿灰塵,「黑壓壓的人群將它踩得粉碎」。這是所有女性狂奔者的必然命運:眾叛親離,一無所有。
卡米爾的悲劇在於,充滿了激情、經常陷於狄俄尼索斯式的醉狂狀態中的她,卻在追求一種阿波羅式的理想--渴望自己的才華像羅丹一樣為社會所承認--在那樣一個男權主宰的世界裏,這無疑是一種烏托邦幻想。她在雕塑方面的天賦簡直不只是才能,而可稱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流,這股洪流時時刻刻激蕩着她的靈魂。可是在一個女人沒有話語權的社會裡,根本就無從得以釋放,而只能被壓制在有限的空間里。而她的另一重悲劇在於,她將那空想維繫在羅丹身上,把他當作打開那個天地的一把鑰匙。她以為在藝術領域內存在着平等。這種企圖超越性別的行為必然會失敗。卡米爾能抓住雕塑的靈魂,卻無法認識到「人世」所必須遵循的遊戲規則。藝術的每一根經脈,每一個細胞都浸潤着男權的控制。女性是被排斥,為中心所拒絕的,她們所追求的藝術在這個社會裡就是屬於男性的。作為一名企圖闖進那個被男人把持的世界的異端分子,卡米爾只能被視為「瘋女人」。她從來就沒有得到「鑰匙」,羅丹對她的「培養」其實是對她的扼殺,加速了她的悲劇命運。如同她的弟弟保羅所說,「所有與生俱來的天賦,只給她帶來不愉快的一切。這完全是大災難,吞沒了我姐姐。」這就道出了那個時代女性最深沉的悲哀:縱使才華橫溢,但由於沒有書寫、言說的權利,也無法得到充分的展露。相反,她們會因為對男性權威的挑戰而面臨着遭受摧殘的更為不幸的命運。只是保羅的這句話中包含着一種宿命感,而卡米爾的悲劇根本不是什麼命運悲劇,而是一出性別悲劇、社會悲劇。
「卡米爾,你只能按我告訴你的去做,你才能成功。」
「我為什麼一定要按你的去做?」
是性別的衝突,同時也是藝術理念的衝突。當導師控制不了學生,當學生要反叛其導師時,愛情關係怎麼能得以繼續?羅丹在質問卡米爾為什麼在作品裏總要表現痛苦時,這位世紀天才顯然沒有耐心和寬容去理解和傾聽另一種愛情方式和藝術表達方式。才華對於女人而言的確是一把刀,可以把生命雕刻得晶瑩剔透,也會把自己割得血肉模糊。在痛苦中體驗甜蜜,在受傷後變得更加堅強。不同的人用這把刀刻出不同的故事。宿命者認為,上天在賜予優厚天賦的同時,也會奪取另一些寶貴的東西。而卡米爾是沒有信仰的人,並不懼怕命運。她其實沒有瘋,也沒有輸給羅丹,她不過是輸給了一個永遠走不出陰影的自己。
她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卡米爾·克洛岱爾,她是個獨立的雕塑家。
在卡米爾與羅丹的作品中,各有一件「雙人小像」,彼此驚人地相似。便是卡米爾的《沙恭達羅》和羅丹的《永恆的偶像》,這兩件作品都是一個男子跪在一個女子面前。但認真來看,卻分別是他們各自不同角度中的「自己與對方」。
更多內容加載中...請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機瀏覽器訪問,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節內容加載失敗,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模式、暢讀模式、小說模式,以及關閉廣告屏蔽功能,或複製網址到其他瀏覽器閱讀!
小說推薦:《落崖三載後》《仗劍獨行斬鬼神》《我不是文豪》《大明漢高祖》《國醫》《從行星總督開始》《滄瀾道》《力速雙A魔法師[西幻]》【大白書】《修仙:我在現代留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