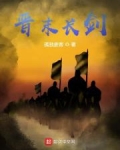董仲舒:巫師與媒婆(1 / 2)
《風流去》轉載請註明來源:繁體小說網ftxs.net
一
十多年前,我在復旦大學聽章培恆先生講「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學」。講到漢代時,章先生說,董仲舒是把君主個人專制與重集體講道德的民族傳統完美結合的人物。這句令我茅塞頓開的話我一直銘記至今。說老實話,作為一名中國古典文學與哲學的教學者和研究者,我以前一直沒能直接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我對漢代經學包括《春秋》學的繁瑣敬而遠之。對董子本人,由一些一知半解而得到的印象也並不太好。上中學時我就知道他為了讀書而三年不窺園的故事,這故事與其說讓我佩服還不如說讓我恐懼,我那時贊成王安石。王安石寫詩諷刺董仲舒,說如果像董氏這樣讀書,倒不如把書全都扔了,然後「杖策遊園日數巡」(《窺園》)。同時,在我的印象里,他還是一個神叨叨怪兮兮的人物,頭腦中裝滿古怪而又可怕的思想,一張口便是陰陽神靈,陰風習習,鬼火閃閃。在志怪類的《幽明錄》《抱朴子·論仙》《神仙傳》《漢武內傳》等等書中,都有他鬼鬼祟祟的影子出沒其中。
我開始較為踏實地讀他的作品,是在1999年。我用的本子是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厚厚的,且密密麻麻的,我的感覺是進入了蟻國。但我可不像那個幸運的唐朝書生盧生。盧生在蟻國里是享盡春光,我在董子的蟻國里卻是弄得焦頭爛額,形神委頓。老實說,這一讀,我很失望。我發現,董子的思想實在很簡樸(如果不是很膚淺的話),他的值得一提的「精華」,也就是我以前在各種間接材料中讀到的那些—在讀過一些相關書籍對他的思想介紹後,再讀《春秋繁露》,確實難有什麼新收穫。一個影響中國封建政治兩千多年的人物,其思想和理論如此貧乏乏味,實在令我驚訝,而我對我們的傳統文化—或稱之為「國粹」—如此簡陋,也很為羞愧。簡言之,董仲舒的所有議論幾乎都可以在先秦諸子那裡找得到,他沒有原創性,只是給我們弄出了一盤大雜燴,大拼盤。更令我驚訝想不通的是,這一盤殘羹冷炙湊成的雜燴,讓我們津津有味地吃了兩千多年,並且竟然還有人想繼續吃下去。
董仲舒在中國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影響深遠,但與之相映成趣的是,他在思想史上卻蒼白而無血色,思想史上的後來者往往對他視而不見,他如同一塊透明的玻璃:人們的眼光從他那兒穿過,如同越過一個虛空。他不能成為思想的資源,董家店裡賣的全是仿製品,二手貨,甚至是破爛貨。我還發現,他的思維能力實在是薄弱,一部厚重的《春秋繁露》,也就是一些比附和類似推理,通過這些似是而非的類似推理和不相關的比附,把這世界一廂情願地想像成一個結構相同的多層復疊的狀貌。在他的著作中,我們找不到因果關係,只有無處無時不在的陰陽關係。他沒有興趣或者沒有能力去探討世界中的因果關係,或者說,他自以為已經一勞永逸地發現了所有的因果關係。他把世界簡單成相生相剋的兩極:陰與陽,二元對稱。可是,我們心裏明白地知道的是,因果關係的思維結構導致科學,導致無限性及對這世界無限性的無限探索;陰陽關係的思維結構則只能導致「玄學」,導致封閉性及世界的重複性,自滿於內心感悟的小聰明,並把這小聰明當作終極大智慧—一個「陰陽」,把一切自然與社會的疑惑都終極性地解決了,也真是大聰明大智慧,但這是不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智慧呢?它是偷懶的大聰明,它只需要感悟而不需要證明,很適合懶惰者的口味。同時它也毫無實際用處,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大智慧」。當然,中國文化往往不以解決問題為目的,而以超越問題為高明。中國文化的粗疏無用以及其無窮的魅力全在於此。直至今日,某些新儒家一邊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一切科學成果,一邊還對西方科學嗤之以鼻:西洋人科學了半天,還是我們祖先早就說過的那個「陰陽」嘛!他們就是不能反思:我們根據陰陽,搞出了什麼科學成果了呢?即便在中國古代,根據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哪一項發明創造,是用陰陽的方法造出來的呢?連有東方文化狂熱的辜鴻銘都承認:「必須承認,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制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中國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麼進步。這不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純抽象科學方面的,諸如數學、邏輯學、形而上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字,是無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中國人的精神》)
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我的腦海中就一再回味着辜氏的這段話,並為之深深嘆息。董子實在是談不上有什麼真正的邏輯抽象思維,談不到真正意義上的形而上學,恰恰相反,他是典型的形下學,實用主義。他的功勞,在於為庸人的笨腦瓜找到了最簡單最好理喻的答案,為聰明人的偷懶找到了最好的遁辭。他通過比附,讓自然與社會、天道與人道,變得有目的,有次序,可理解了。把複雜的世界與世界上無窮盡的問題絕對地簡單化了—不就是「陰陽」么!那麼簡單的世界,那麼簡單的本質,那麼簡單而明晰的意義,我們無須思想它。世界的目的性如此明白和簡單,思想顯得多餘。他幾乎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所有科學問題,科學顯得不必要。至於基礎科學,要麼不必要,要麼把它實用化,甚至乾脆變成政治—中式的天文學就是這樣由自然科學變成政治的。陳炎先生曾正確地指出:在中國,「指南針不是電磁學,造紙術不是物理學,傳統的火藥不是依據化學方程式配製出來的,而活字印刷也用不着電子科學的參與……如此說來,我們長期以來引以為自豪的『四大發明』並非理論科學,而是工藝技術!」(《積澱與突破》)
讀董子的文章,我的思想如同在溜冰—我們在冰面上順溜地滑行,幾乎沒有什麼障礙需要我們克服,但我們卻什麼也沒有得到,我們遠遠不能哪怕是蜻蜓點水式的接觸事物的真正本質。他的語言和思維使事物的表面凍結起來,讓我們通過,我們一下子就跨越了千山萬水,但我們卻沒有摘到一片真正的翠綠的葉或紅鮮的果,也沒有啜飲到一滴真正的水。他使我們民族在自然科學上懵懵懂懂心安理得地偷懶了兩千多年,又讓我們在等級社會中各得其所心甘情願地生活了兩千多年。他是一個巫師,一個僅用「陰陽」兩個字的咒語,讓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沉睡兩千多年的巫師!
二
一個稍具現代科學觀念的人(不論他是否有,或有多少具體的科學知識),讀董仲舒的著作,都會感到乏味透頂。他那麼自信,他自信他發現了自然人生的永恆之道,並且這道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這又讓我們覺得好笑。這是一個絕對不幽默的人弄出的大滑稽,所以,我們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不知道該顯示什麼樣的表情。
在中國古代,先秦而後,凡被稱為「大儒」「純(醇)儒」的人,都不可愛。董仲舒就是被班固稱為「純儒」,又被朱熹稱為「純粹」的人。老實說,他確實沒有什麼可愛的地方。我們知道,孔子是整日和弟子們廝混在一起的,想笑便笑,想哭便哭,想唱便引吭高歌一曲,感觸便涕泗滂沱一番,歌哭自如,幽默風趣,甚至拿弟子們開開心,和他們打打嘴仗,高興了便誇他們幾句,不高興了便斥喝幾聲,這是一個家常的老頭,可敬更可愛。而董仲舒傳授弟子,卻是深居簡出,和弟子們不打交道,弄得壁壘森嚴。後來的弟子們更是面都不讓見—他讓他的幾個高足代他設席授課。高年級教低年級,就一直這麼「次相授業」。架子端得大,面目弄得玄,人蹤變得神,儼然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教主。所以他不可愛,而可笑。他幹什麼事都那麼認真,那麼自信正確,所以他毫不馬虎,一絲不苟,但從我們今天看來,在很多事情上他是絕對錯了。既如此,他那種認真不敷衍,嚴肅不馬虎就顯得十分可笑了。寫到這裏,我向讀者承認,讀《春秋繁露》,我一直皺着眉頭,捺着自己的性子,以使我不把這本書扔到窗外去。但讀到後來,有兩篇文章還是讓我粲然一樂:《求雨》《止雨》。並且越讀越樂,樂不可支。
我們是農業國。雨水直接影響着國民經濟,從而影響着政治。就此一點說,說中國的政治是雨水政治,也不算過分。幾千年來的多次政治動蕩與內戰,都與旱澇災害有關。《漢書》在記載董仲舒的一生功績時,專門講到了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照班固的看法(司馬遷《儒林列傳》竟也如此吹捧他的老師),則董仲舒已經徹底解決了旱澇自然災害問題,只要我們學用董氏的求雨止雨之法,要風得風,要雨即雨,要晴即晴。這實在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福音了!從此吾華夏神州真變成天國了!
這種神話一般的記載出現在中國兩個最誠實的史學家筆下,讓人有些不可思議。尤其是司馬遷。他本來極具理性精神。在《五帝本紀》中,他說:「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難道說董仲舒能隨心所欲地指揮上天下雨或放晴,這樣的「言」就「雅馴」了?如果不是董仲舒自己記錄他如何求雨、止雨方法的文章至今還保留在《春秋繁露》中,出於我們對司馬遷、班固的信任,我們可能真會以為一種偉大的技術失傳了呢。那麼,在他的這兩篇文章中,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記載呢?
董仲舒對自己求雨止雨的理論根據及具體操作步驟的合理性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對求雨止雨的效果也應該是深信不疑的。不知道上天是否真的每次都照顧了他的自尊心,他要雨,便給他落水滴,他要晴,便給他出日頭。看他的《求雨》篇,說到春夏秋冬四季求雨,各有不同的操作方法,如何祭祀,祭品都需要什麼,選什麼樣的人向上天陳辭等等,非常具體,極其認真。此時的董仲舒,哪裡是學者、思想家?完全是一個巫婆神漢、江湖騙子。看他那麼煞有介事地做一件不可能有結果的事,真為他感到累,又感到好笑,同時還有一絲同情,以及對不能應驗時他內心所要經歷的創痛的擔憂:如果像《詩》所云,他那邊「其雨其雨」的禱告不止,這邊老天爺偏偏「杲杲出日」,他一張老臉往哪擱?在那麼多奉他為神明的地方官吏和百姓面前,他如何走下神壇?他憑什麼那麼自信呢?他的依據是那麼薄弱,是那麼想當然。他從他的陰陽理論出發,認為大旱是由於陽氣太甚陰氣不足引起的,所以要燒化公豬、公雞,要埋死人骨頭,說這是為了閉陽;他要通橋之雍塞不行者,要決瀆(挖開水溝),要開山淵(掘開山泉),說這是為了縱陰。他禁止男人們出門上街,禁止他們相聚飲酒,這還是閉陽;要發動女子們滿街跑,要她們滿面春風,歡歡鬧鬧,這又是縱陰。最後他有一個總括性的一般要求或注意事項:無論哪個季節求雨,都要選在水日進行—
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
而下面這一句更讓我噗地笑出聲來—
令吏民夫婦皆偶處。
原來,男女行房也是求雨不可缺少的一環!這也是雨露滋潤的氣象么!看來天下雨便是天和地在做性事。真是妙不可言!而一想到求雨那一天的晚上,為了激起天老爺的「性趣」,也為了響應政府的號召,所有成人男女都一齊干那事,就更令人忍俊不禁。這董仲舒治理下的國家,真是奇風異俗啊。讀到此處,我迫不及待地翻到下一篇:《止雨》,看看他若要止雨,是否要禁男女之事?果然!除了其他諸項和「求雨」正相反,要縱陽閉陰,從而要女人藏起來,男人滿街跑外,赫然的就是一句:
書七十縣,八十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歸。
—通告七十縣,八十鄉,以及官職在千石以下的,夫婦在官署同居者,全都把老婆趕回家去,暫停男女,免得引得天老爺縱淫不止(當然,千石以上的大官仍然可以行雲布雨,這與多年前我們規定只有副廳級以上幹部才可以讀《金瓶梅》一樣有道理)!
看到這裏,我不無小人之心地想:這董仲舒平時奉為至尊,讓人頂禮膜拜的「天」,怎麼好像是一個愛看黃色錄像並且不能自控的傢伙?!
至此,我想讀者會有同我一樣的感覺: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確實有不少荒唐的東西。不過,一種文化中有一些很荒唐的東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荒唐的東西竟成為該種文化的根基。那這座文化大廈就太脆性、太淺薄、太庸俗、太簡陋了。董仲舒是被人稱為「封建理論大廈的構建者」的,而他的理論構想後來也確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原則,成為世俗政權的理論支柱,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理論、什麼樣的原則啊,我看這實在不能叫「國粹」,叫「國丑」還差不多。我真怕哪位新儒家又把它當作寶貝張揚出去。這可叫我們怎麼做人哩。
三
更多內容加載中...請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機瀏覽器訪問,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節內容加載失敗,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模式、暢讀模式、小說模式,以及關閉廣告屏蔽功能,或複製網址到其他瀏覽器閱讀!
小說推薦:《不可以離婚》《我在大夏竊神權》【抖音書院】《早春晴朗》【文明小說】《一個俗人的諸天影視之旅》【小燕文學】《在北宋當陪房》【全本迷】《1978合成系文豪》
本章未完,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若瀏覽器顯示沒有新章節了,請嘗試點擊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單,退出閱讀模式即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