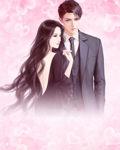異地求學
天才一秒記住【繁體小說網】地址:ftxs.net
異地求學
1893年,魯迅家裡出了一件大事,這場風暴徹底毀掉了周家的安樂世界;從此和平與安寧被敗落與苦難代替了。這場災難來源於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應親友之求,同時也是為了兒子周伯宜而去賄賂鄉試的主考官,不幸的是事情敗露而被關進大牢,家裡每年要花大筆錢去通融,於是全家收入的錢財都來填這個無底洞了。幾年下來,周家錢財花完了,也就破落了。
魯迅兄弟為了防止受迫害,在祖父被通緝期間,只好跑到外婆家避難。但這次卻不是看到一張張的笑臉,往日巴結他們的一些人,現在說他們是「乞食者」,後來逃難到舅父家,看到的也是這種世態炎涼,到處遭到侮辱和蔑視。只有勞動農民和他們的孩子,同過去一樣熱情。家庭的變故,使小魯迅深刻地認識了這個社會。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不久就得了重病。
他由於與這場案有牽連,不僅不允許考試了,連原來的秀才身份也被革掉了。他本來就不善於持家,這回為了營救老父親,家裡生活的重擔又壓在他身上,眼睜睜地看着家裡的財產和土地都沒了,十分焦急,脾氣更壞了,酒也喝得更凶了,終於得了嚴重的肺病。
長子魯迅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營救祖父、為父親治病,都需要錢,山窮水盡的他只好每天都去當鋪,把衣服或首飾送上比自己高一倍的櫃檯,在誣衊中接過一點可憐的錢,然後再到藥房裡,在和他一樣高的櫃檯前,給久病的父親買葯。
在家庭沒落的凄涼氣氛中,這種愁苦掙扎的滋味是難受的,他不能不感到這人世的痛楚與冰冷。
這時的魯迅已早早地告別了天真年代,無心與孩子們一樣嬉鬧了。
擺在魯迅面前的現實是如此嚴峻,他該何去何從呢?他應該繼續通過科舉而走仕途嗎?
家已經破落了,17歲的魯迅被迫去尋求新的路。
當時清政府還是科舉取士,考八股文和試帖詩。讀書人可以參加「院試」、「鄉試」和「會試」,最後取得進士的功名,才能做官。他的祖父就是被這條路托起,又被這條路摔進牢獄的。但魯迅的家境,已不允許他走這條路了。
還有一條破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的道路,去學做生意或學當「師爺」,這也是魯迅不願意的。
還有一條被世人稱為異端的路,那就是學洋務,中國自古認為「好男不當兵」,當時開的洋學堂有軍事類的,不收學費,每月還給津貼,這很適合魯迅,但走這條路卻要被人笑話,被認為是把靈魂賣給洋鬼子了,受到加倍的奚落和排斥。
但是魯迅有一個小叔父在1897年考入了一個南京水師學堂,給了魯迅一些鼓舞,他並不是想學海軍,只是由於不收學費就能讀書。他就決定去那裡了。
走出這一步,受到了還被押在獄中的祖父的反對,他指令魯迅兄弟學做應考的詩文,親自評閱圈點,希望他們能科場得意、官運亨通。母親也為了兒子要離鄉背井,不走「正路」而心酸。
但魯迅已義無反顧了,他寫信告訴祖父:「欲往金陵,已說妥。」措辭堅決。母親沒有辦法,只好變賣首飾,籌集了8元路費。
1898年5月1日,魯迅決定遠走,告別了從小生活的地方,也告別了苦樂參半的少年時代。家鄉的河水,把他送到上海,又乘船沿着長江逆流而上。離開朝夕相處的母親和弟弟,離開了故園,他開始了自己的青年時代。
大約7天後,他來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那一天正是震動中國的戊戌變法的前夜,再過1個多月,即是6月11日,光緒皇帝就要下詔「明定國是」,開始維新運動了。
魯迅來到江南水師學堂,這裏是洋務派為了訓練水兵而建立的。魯迅之所以會選擇這裏,是因為他的一個名叫椒生的叔祖,在這裏做管輪班的監督,是州縣一級的官吏。魯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這個叔祖家,稱周椒生為慶爺爺,他是周氏家庭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這位自己在水師學堂當官的叔祖,卻對這種洋務學堂極為蔑視,是個很保守頑固的人。他平時愛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綢的「接衫」,長長的兩色綢衫,肥肥的袖子,是忠於傳統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還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凈室里跪誦幾遍《太上感應篇》。
他覺得自己的本家侄孫,竟窮酸到付不起學費,未能走科舉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這裏來準備當一名搖旗吶喊的水兵實在很不體面,為了不給九泉之下的祖宗丟臉,他覺得魯迅不宜使用家譜中的名字,就這樣,他把「豫才」改名為「樹人」。魯迅萬萬沒想到,身在水師學堂的叔祖,竟是這樣瞧不起學習洋務。
但這個學堂並不是魯迅夢想的那樣,並不是不同於他所見到過的「別樣的人們」,學校里死水一般的生活乏味到極點,一個星期有4天讀英文,1天讀《左傳》,1天讀漢文。那些老先生們對於新知識一竅不通,對於新名詞、新概念總是望文生義,連「地球」是什麼東西也搞不清楚。
更多內容加載中...請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機瀏覽器訪問,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節內容加載失敗,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模式、暢讀模式、小說模式,以及關閉廣告屏蔽功能,或複製網址到其他瀏覽器閱讀!
《文學藝術家》轉載請註明來源:繁體小說網ftxs.net,若瀏覽器顯示沒有新章節了,請嘗試點擊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單,退出閱讀模式即可,謝謝!